体内微流变学揭示了三维细菌生物膜内部的局部弹性和塑性响应
可靠 创新 同行 发展
细菌生物膜是大量存在的三维活性物质,具备执行复杂的生物力学和生物化学功能的能力,包括可编程生长、自我修复、过滤以及生物生产。然而,一直以来,都缺少能够在细胞尺度上具备空间分辨率的在体测量生物膜内部力学特性的方法。在此,在不同的应力振幅、周期和生物膜大小的各种条件下,在施加剪切应力期间和之后,对霍乱弧菌的活体三维生物膜内的数千个细胞进行了追踪,这揭示了细胞位移和细胞重新定向的各向异性弹性和塑性响应。利用细胞追踪来推断通用力学模型的参数,获取了生物膜内部弹性模量的空间分辨测量值,其与生物膜基质内多糖的空间分布存在关联。此处引入的无创微流变学和力推断方法为研究活体材料中具有高空间分辨率的力学性能提供了一个通用框架。
据估计,细菌生物膜群落乃是地球上最为丰富的生物材料,且在人类健康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涵盖从肠道微生物组到各类感染。于生物工程和材料科学中,生物膜当下正作为典型的可编程多功能活性材料而被深入探究,其整合了机械稳固性与适应性,以及自我修复和化学合成的能力。尽管生物膜是具备广泛技术潜能的材料,然而在医疗场所和工业管道里,细菌生物膜亦可能构成问题,因为它们对于抗生素、消毒剂和机械应力具有高度的耐受性。故而,控制生物膜的生长和机械性能对于技术应用以及清除感染和工业中不受欢迎的生物膜而言,乃是重要的挑战。
生物膜通常为在表面生长的三维结构,其生长方式或是消耗表面内的营养物质,或是消耗表面上方水相中的营养物质。在细菌生物膜中,细胞借助由蛋白质、核酸、多糖和脂质构成的自身产生的细胞外基质彼此相连并附着于表面,共同形成一种复杂且具备机械弹性的材料结构。不同细菌物种的生物膜,其基质的确切分子组成存在差异。生物膜去除所具有的工业和医学重要性致使针对宏观尺度(100 μm - 10 cm)下整个生物膜的整体材料特性展开了多项研究,明确了特定基质成分的重要作用。依据生物膜的整体材料特性,强流体流动已被证实会显著改变生物膜的形状,包括对于产生粘弹性生物膜的细菌物种形成生物膜飘带。
尽管针对整个生物膜的全球材料属性已获取了重要的洞见,但对于生物膜内材料属性的空间分布及其后果却知之甚少。对生物膜中基因表达的空间分辨测量显示,在细胞长度尺度上存在显著的生理异质性。再者,生物膜内部的基质成分在细胞长度尺度上也存在变化。生物膜中的机械性能很可能在细胞长度尺度上也有差异,然而在这些微观尺度上,基质成分的空间分布与局部材料属性之间的关系仍未可知。
为探究生物膜内部具有空间分辨率的材料特性,此前的研究已在生物膜内部置入微观珠子。珠子的被动扩散或在主动扰动后的位移,可用于推断珠子周边的机械环境。与置于生物膜内的微珠不同,细菌细胞通过其细胞表面自身产生的蛋白质和多糖,锚定在细胞外生物膜基质上并彼此相连。因此,相较于微珠,细菌细胞或许能更精准地示踪生物膜内部的局部材料特性。基于这一理念,我们试图以细胞分辨率无创地测量 3D 细菌生物膜的局部机械特性。为达成此目的,我们将高度可重复的微流控生物膜培养系统与流量控制,同 3D 活细胞显微镜技术的最新进展以及基于深度学习的高精度细胞检测图像分析相耦合。
我们的实验平台能够让我们在各种不同的剪切速率振幅、暴露时长以及生物膜尺寸的广泛范围内,追踪霍乱弧菌 3D 生物膜中的单个细胞在强流体剪切期间及之后的情况。为重构生物膜的内部材料特性,我们研发了一种计算推断方法,用于从细胞追踪数据估算弹性力。依据实验中的细胞坐标变化,我们还能够以细胞分辨率量化生物膜内部的可塑性,其被定义为生物膜在暴露于流体剪切前后结构上的差异,这可由细胞位置和方向的改变来确定。我们的测量结果揭示了生物膜中机械刚度的空间分布与细胞外基质特定分子成分的空间分布之间存在关联。除了提供细菌生物膜内部局部弹塑性应力响应的精细分辨图像之外,在此开发的综合实验和计算方法能够为细胞水平分辨率下生物材料的无创流变学分析奠定基础。
为了研究生物膜的机械性能,我们在微流体通道中培养霍乱弧菌生物膜,从单个细胞生长到 521 - 9554 个细胞的群落规模,其中最大的细胞数量对应的生物膜菌落近似半球形,直径为 50 微米,高度为 17 微米,体积为 5246 微米3。在生物膜培养期间,细胞在极低的剪切速率(通道底面处的剪切速率为 20.4 秒?1)下持续暴露于最小 M9 培养基的恒定流动中,这种环境条件导致生物膜内细胞的中位体积为 0.5 微米3。然后我们停止流动,并进行了以下实验。我们获取了生物膜中所有细胞的三维高分辨率图像,然后提高微流控通道中的流速,以获得剪切速率 = 8.16×10^4 s^?1(通道中的平均流速:uaverage = 0.95 m s^?1),然后我们又获取了另一幅三维图像。在施加这种强剪切速率特定时间(3 - 40 分钟)后,我们再次停止流动,并获取了生物膜的最终三维高分辨率图像。
图1,生物膜因剪切流变化引起的变形、恢复和可塑性。A)在微流控通道中附着于玻璃表面的霍乱弧菌生物膜菌落(5013 个细胞,V = 3891 μm3)在单细胞水平上进行了 3D 成像,以追踪强剪切流(剪切速率 8.16 × 10? s?1)作用引起的结构变化。根据细胞与 z 轴的角度对细胞进行着色。第一个 3D 图像时间点称为“之前”,是在通道中无流动的情况下获取的。获取第一个 3D 图像后,流速从 0 增加到 2000 μL min?1 并保持一定时间(3 - 40 分钟)。第二个 3D 图像时间点称为“变形”,是在强流沿 x 轴施加 1 分钟时获取的。第三个 3D 图像时间点称为“之后”,是在强流再次停止 1 分钟后获取的。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前两个时间点之间的生物膜结构变化称为“变形”,后两个时间点之间的称为“恢复”,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时间点之间的称为“可塑性”。B)基于两个时间点之间的 3D 拟共形映射,使用细胞质心坐标计算生物膜变形(左)、恢复(中)和可塑性(右)的应变场幅度(I1 = εxx + εyy + εzz)。来自 n = 9 个独立重复生物膜的平均结果显示在一个半椭圆形区域上,为了可视化内部,去除了四分之一。C)生物膜变形,在 xz 平面(上)和 xy 平面(下)可视化:流体剪切速率从 0 增加到 8.16 × 10? s?1 引起的平均细胞位移的矢量场。对于 xy 平面矢量场,包括所有 z 坐标处的细胞位移进行平均。对于 xz 平面矢量场,包括所有 y 坐标处的细胞位移进行平均。D)生物膜恢复,在 xz 平面(上)和 xy 平面(下)可视化:流体剪切速率从 8.16 × 10? 降低到 0 s?1 后平均细胞位移的矢量场。E)生物膜可塑性,在 xz 平面(上)和 xy 平面(下)可视化:平均细胞位移的矢量场。在(C - E)中,位移矢量λ的单位在所有图中是一致的,但按每个图的插图所示进行了缩放。对于(C - E),使用了来自 n = 87 个独立重复生物膜的数据,首先通过将每个生物膜的大小按半径 R 进行归一化,然后在所有生物膜中对大小为 0.05×R 的空间箱中的细胞位移进行平均。
利用细菌单细胞分割以及一个涉及应变场计算的迭代跟踪算法(图 1B),该算法是专门为我们实验生成的图像数据集开发的(见实验部分;以及支持信息中的图 S1),我们在所有三个时间点跟踪了 274 个独立的生物膜中的细胞。基于这些细胞轨迹,我们计算了在将剪切速率从 0 增加到 8.16×10^4 s^?1 引起的生物膜变形期间(图 1C),以及在将剪切速率从 8.16×10^4 降低到 0 s^?1 引起的生物膜恢复期间(图 1D)的细胞位移。通过将生物膜恢复后的细胞位置与其初始位置进行比较,我们能够研究并量化局部生物膜的可塑性(图 1E)。在恢复期间,细胞位移的大小(但方向相反)与变形期间的细胞位移相似,导致流量降低后的生物膜形状看起来与流量增加前的生物膜形状相似。然而,在变形和恢复期间,一些最外层的细胞已被撕裂,并且剩余附着的细胞存在净细胞位移。总之,这些结果表明生物膜表现出较大的弹性响应,塑性成分较小(图 1C - E)。
Video 1: 在剪切速率从 0 增加到 4.08×10^4 s^-1 ,然后再降低回 0 s^-1 的过程中对霍乱弧菌生物膜变形的可视化。该视频包含 81 个时间点,在每个时间点,我们获取了一个 z 间距为 400 纳米的完整共聚焦 3D 图像。在每个成像时间点,剪切速率是恒定的。然而,在每个成像时间点之间,剪切速率会增加或降低:在时间点 1 - 41 之间,剪切速率从 0 以 0.102×10^4 s^-1 的增量增加到 4.08×10^4 s^-1 ;在时间点 41 - 81 之间,剪切速率从 4.08×10^4 以 0.102×10^4 s^-1 的增量降低到 0 s^-1 。为了尽可能减少光暴露和光损伤,我们通过向流入的 M9 培养基中添加一种 DNA 结合染料(Syto 9 绿色荧光核酸染色剂,5 μmol/l,西格玛),从细胞中产生了高荧光信号。在生物膜变形期间的多个时间点获取 3D 图像使我们能够更容易地追踪细胞。然而,我们注意到,长时间暴露于 DNA 结合染料会导致生物膜大幅软化,这使得该技术无法常规用于表征生物膜的机械性能。
图2,生物膜的结构在变形、恢复和可塑性过程中在细胞层面发生变化。A)本研究中坐标的示意图:流动沿 x 轴方向;灰色半球表示生物膜形状;在流动之前、期间和之后的细胞质心 xyz 坐标分别描述为 r1、r2 和 r3。B)θz 的定义和沿细胞主轴的单位向量 n 的示意图,用于局部向列序参数 Sk 的定义,该参数是针对所有索引为 l ∈ L 且位于索引为 k 的焦点细胞表面 1.8 μm 范围内的细胞计算的。C)生物膜变形、恢复、可塑性的侧视图(xz 平面),针对四个单细胞层面的结构参数(Δr,位移;(r × Δr)y,角动量类位移叉积的 y 分量;Δθz,细胞主轴与 z 轴夹角的变化;ΔS,局部向列序参数的变化)。D)生物膜变形、恢复、可塑性的顶视图(xy 平面),针对四个结构参数(Δr,r × Δr,Δθz,ΔS)。在(C)和(D)图中,对 n = 13 个独立的生物膜的生物膜结构变化进行了测量,这些生物膜体积 V > 2800 μm3,暴露于剪切速率 = 8.16 × 104 s?1 持续 20 或 40 分钟。
单细胞水平生物膜结构参数的测量结果表明,在变形和恢复细胞位移最大的位置,塑性细胞位移最大。然而,与变形和恢复细胞位移相比,塑性细胞位移相对较小。相比之下,细胞取向和向列序参数的塑性变化与变形和恢复过程中这些参数的变化幅度相似。
图3,相图展示了最大流速和生物膜体积对生物膜变形、恢复和可塑性过程中结构变化的影响。A)变形过程中的生物膜结构变化。每个热图显示了最大流速和生物膜体积 V 对生物膜结构参数(Δr,细胞位移;|(r×Δr)y|,类似角动量的位移叉积;|Δθz|,细胞与 z 轴排列的变化;|ΔS|,局部向列序的变化)的影响。热图中的每个像素是在此条件下所有生物膜中所有细胞的平均值。B)恢复过程中的生物膜结构变化(将剪切速率从最大值降低回 0 s?1 之后)。C)表征可塑性的生物膜结构变化。对于每个热图中的每个像素,来自 n≥3 个独立复制生物膜的数据取平均值。
为了确定我们系统的哪些特性会影响生物膜结构变化的幅度,我们对不同体积的生物膜、不同的最大剪切速率以及在最大剪切速率下的不同暴露持续时间进行了类似的测量。对于这些实验中的每一个,我们随后计算了 Δr、|(r × Δr)y|、|ΔS| 和 |Δθz|,作为所有重复生物膜中所有细胞轨迹的平均值。这些实验表明,对于生物膜的变形(图 3A)、恢复(图 3B)和可塑性(图 3C),较大的剪切速率和较大的生物膜体积通常会导致更高的细胞位移参数(Δr、|(r × Δr)y|),但 Δr 可塑性除外,其并不强烈依赖于生物膜体积。有趣的是,这些实验还表明,细胞取向的最大变化(|ΔS|、|Δθz|)发生在小体积的生物膜和大剪切速率的情况下(图 3)。小生物膜表现出强烈的细胞取向变化,因为其表面积与体积之比大,并且更大比例的细胞直接经历流体剪切。然而,体积小的生物膜不会表现出大的细胞位移,因为它们的高度相对较低,细胞的 z 位置是细胞位移的关键决定因素(图 1C - E 和 2C)。对于四个参数(Δr、|(r × Δr)y|、|ΔS|、|Δθz|)中的每一个,在变形(图 3A)、恢复(图 3B)和可塑性(图 3C)中,生物膜体积与剪切速率热图的模式是相似的。无论生物膜体积如何,最大剪切速率的值是变形、恢复和可塑性过程中结构变化幅度的关键控制参数(图 3)。
生物膜中弹性模量的空间分布
在变形和恢复过程中,生物膜结构的变化幅度相似但方向相反,这表明生物膜对剪切流的响应存在弹性成分(图 1C - E 和 2C、D)。为了推断生物膜内弹性模量的空间分布,我们将细胞位移的空间分辨测量结果与以弹性模量为参数的生物膜通用力学模型结合使用。对于此模型,在施加流动之前,我们根据实验确定的每个细胞的细胞质心坐标创建了一个 3D 德劳内三角剖分,并假设三角剖分中由边 e = (i, j) 连接的所有相邻细胞质心 i 和 j 都通过一个未知刚度 ke 的弹簧连接,弹簧具有静止长度 (图 4A,见实验部分)。在强剪切流期间,生物膜变形,我们使用实验中的细胞追踪数据来测量每个弹簧的最终长度 le。系统的弹性能为 ,对于生物膜内部坐标为 ri 的每个细胞 i,弹性力平衡,使得 ?H/? ri = 0。重要的是,弹性力仅在生物膜弹性内部的细胞之间平衡,而对于生物膜边界部分的细胞不平衡,这些边界细胞会受到流体剪切力或细胞与基底表面的粘附力。为了推断生物膜内部的弹性特性,不需要为生物膜边界上的细胞明确建模这些外力。然后,我们针对生物膜中弹性模量 的空间分布求解此模型,仅寻找连续变化的解(见实验部分)。我们通过展示该框架能够基于实验确定的细胞质心位置准确恢复我们在模拟生物膜中指定的弹簧刚度(ke)和模量来证明其稳健性。
图4,生物膜中物质特性的空间分布与细胞外基质成分的空间分布相关。A)用于推断机械特性空间分布的模型示意图:在该模型中,在德劳内三角剖分中为相邻的细胞质心通过未知刚度 k 且静止长度为 l0 的弹簧连接。然后,我们使用流动前和流动期间细胞位置的实验测量值,以及生物膜内部细胞的力平衡条件,来推断生物膜内部相对弹簧模量的空间分布,而没有明确模拟生物膜边界部分细胞的流体 - 细胞或细胞 - 基底表面相互作用(见实验部分)。B)具有归一化 xy 径向位置和归一化 z 位置的弹簧模量 kl0 的空间分布。数据是对 n = 10 个独立的重复生物膜进行平均。热图底部的灰色区域表示直接附着在基底表面的细胞(0 ≤ z/Rz ≤ 0.0453)所占据的区域,对于该区域,我们的模型无法提供弹簧模量。C)使用免疫荧光和共聚焦显微镜测量的生物膜内基质蛋白 RbmC 的空间分布。RbmC 的其他数据见图 S11A(支持信息)。数据使用与(B)中相同的坐标系绘制。D)使用免疫荧光测量的基质蛋白 Bap1 的空间分布。Bap1 的其他数据见图 S11B(支持信息)。E)使用免疫荧光测量的基质蛋白 RbmA 的空间分布。RbmA 的其他数据见图 S11C(支持信息)。F)使用荧光共轭凝集素测量的基质多糖 VPS 的空间分布。正如在图 S12(支持信息)中 VPS 标记的原始图像所示,即使在没有细胞附着的区域,凝集素也优先附着在玻璃表面。来自玻璃表面的这种信号泄漏到生物膜的较高区域,因此我们无法准确确定灰色区域中的 VPS 丰度。每个基质成分的数据是对≥ 3 个独立的重复生物膜进行平均。每个基质成分的颜色标度是背景扣除后的荧光强度。
细胞外基质成分的空间分布解释了弹性模量
我们假设弹簧模量的空间模式是由自产细胞外生物膜基质成分的变化引起的。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测量了霍乱弧菌生物膜主要基质成分的定位和丰度:蛋白质 RbmA、RbmC、Bap1 和弧菌多糖(VPS)。为了使用共聚焦显微镜直接对基质成分进行成像,我们使用了与荧光染料偶联的针对 RbmA、RbmC 和 Bap1 的抗体,以及与荧光染料偶联的针对 VPS 的凝集素。
这些实验表明,对于我们微流体系统中的生物膜,RbmC 在生物膜底部边缘附近含量丰富(图 4C),Bap1 位于生物膜底部表面和暴露于流体的外边缘附近(图 4D),RbmA 在生物膜面向流体表面的区域高度丰富(图 4E)。缺乏 RbmC 或 Bap1 的突变体形成的生物膜对高剪切速率具有显著的抗性。没有 RbmA 的生物膜在高剪切速率下很容易从表面剥落,这表明该蛋白质对于生物膜的机械凝聚力很重要,可能是由于其交联了长链多糖 VPS。然而,基质蛋白 RbmC、Bap1 和 RbmA 的空间分布与弹性模量的空间分布没有定性的相关性。相比之下,细胞外基质多糖 VPS 显示出与弹性模量密切相关的空间分布(图 4F),这表明 VPS 的丰度是决定生物膜弹性细胞 - 细胞相互作用和对剪切流的整体弹性响应的关键因素。
通过使 3D 霍乱弧菌生物膜经受剪切流的增加和减少,并追踪由此产生的单个细胞位移和细胞重新定向,我们能够进行空间分辨的体内流变学测量。尽管存在强剪切速率(= 8.16 × 104 s?1)和剪切应力(τ = 69.7 N / m?2),对应于微流体通道中的平均流速 Uaverage = 0.952 m / s?1,但生物膜对剪切流的增加仍然具有显著的弹性。生物膜内的细胞位移轨迹显示出弹性响应,以及约为弹性响应 1/3 大小的塑性响应。细胞定向也显示出与弹性响应大小相似的塑性响应。此外,生物膜内的弹性和塑性响应在空间上是异质的。
3D 生物膜内弹性响应的空间变化使我们推测这些群落内部的弹性模量也在空间上发生变化。通过假设基于连接相邻细胞的弹簧网络的生物膜通用力学模型,我们使用我们的细胞位移轨迹来获得生物膜中细胞 - 细胞相互作用的弹簧模量的空间分辨图。弹簧模量的空间分布与连接生物膜局部分子组成与微观细胞轨迹和细胞群落的介观材料特性的基质多糖 VPS 的丰度密切相关。我们在细胞尺度上对空间变化的材料特性的观察补充了以前没有空间分辨率的生物膜流变学的宏观表征。
我们基于结合实验细胞追踪数据和通用弹簧网络模型开发的用于推断细菌生物膜体内内部弹性特性的方法,可用于推断任何可以进行细胞分辨率成像的不均匀弹性生物材料的内部特性。由于 3D 活细胞显微镜技术的最新改进和基于神经网络的图像分析能够为许多其他生物系统获得单细胞水平的数据,我们预计我们的推断框架将广泛适用于细胞尺度上生物材料的体内流变学分析。
在生长过程中,生物组织和微生物群落消耗营养物质并产生废物,这建立了资源梯度和局部变化的微环境,最终导致局部变化的基因表达和局部变化的基质成分产生。由于这些资源梯度预计不会随时间保持恒定,我们预计生物膜的材料特性不仅如本研究所示在空间上是异质的,而且在时间上也是异质的。生物膜的时空材料特性的全谱尚未得到表征,这可能为通过机械剪切去除生物膜以及设计具有可调剪切响应的生物材料揭示机会窗口。
Video 2: 使用 0.1 微米的荧光示踪珠,对微流控通道中霍乱弧菌生物膜菌落周围的流动情况进行了可视化展示。视频中的不同画面帧对应着通道中不同的 z 高度(z 位置在左上角标明)。对于通道中的每个特定 z 位置,视频的每个画面帧都展示了示踪珠的原始荧光图像(左)、带有叠加流场矢量的生物膜原始荧光图像(中)以及生物膜周围的流速(右)。
细菌培养与生物膜生长
本研究中使用的主要菌株源自霍乱弧菌 N16961 野生型,通过引入赋予粗糙度的 vpvCW240R 等位基因,并引入导致直杆状细胞形状的?crvA(VCA1075)突变。该菌株还含有一个质粒(pNUT542),该质粒带有庆大霉素抗性和一个无 lacO 的 Ptac 启动子,以驱动 sfGFP 的组成型产生。所得的细菌菌株称为 KDV613,[52]并用于本研究中的所有剪切流变形实验。本研究中使用的其他菌株均为 KDV613 的衍生物,但 KDV2013 除外,它含有不同的质粒。霍乱弧菌生物膜在 M9 基本培养基中生长,该培养基补充有 2 mM MgSO4、100 μm CaCl2、MEM 维生素(Sigma)、0.5% w/v 葡萄糖和 15 mM 三乙醇胺(pH 7.1)。LB 培养基用于过夜培养,包含 10 g L?1 胰蛋白胨、5 g L?1 酵母提取物和 10 g L?1 NaCl。此外,向 LB 和 M9 培养基中加入 30 μg mL?1 庆大霉素,以维持质粒 pNUT542。
产生 sfGFP 的霍乱弧菌生物膜在微流控流动室(室尺寸:[宽度;高度;长度] = [500;70;7000] μm)中生长。流动室由通过氧等离子体与玻璃盖玻片结合的聚二甲基硅氧烷构建而成。微流控设计在每个盖玻片上包括四个独立的通道。这些微流控通道的制造过程保证了高度可重复的通道尺寸和表面特性。每个通道都接种了霍乱弧菌菌株的培养物,培养物的制备如下:在液体 LB 培养基中于 28°C 振荡条件下过夜培养,早晨在 LB 培养基中以 1:200 回稀释,并培养至 600 nm 处的光密度为 0.5。该培养物用于接种流动通道。通道接种后,1 小时内不启动流动,以允许细胞牢固地附着在表面。然后,以 100 μL / min?1 的流速将液体 M9 培养基通过通道推送 45 秒,以洗去非粘附细胞并从通道中去除 LB 生长培养基。然后将通过通道的流速设置为 0.5 μL / min?1,以连续向通道供应新鲜的 M9 培养基,使表面粘附的单细胞生长为生物膜。通道接种后的流速和生物膜生长期间的流速使用高精度注射泵控制。
不同流体剪切力的实验
霍乱弧菌生物膜在微流体流动室中培养,存在低流速(0.5 μL min?1,20.4 s?1),该流速由注射泵控制。在生物膜高度 Rz 达到约 10 - 30 μm 后,将注射泵与流动室的入口断开,并由微流体压力控制器(OB1 MK3+,Elveflow)取代。该压力控制器通过整合来自流量传感器(MFS5,Elveflow)的反馈,能够向微通道施加更高且更稳定的流速。流速、显微镜载物台和 3D 共聚焦成像通过使用 MATLAB 控制 μManager[63]和流量控制软件(ESI,Elveflow)同时进行控制。为了在强流实验期间抑制蛋白质产生和细胞分裂,在 M9 培养基中加入两种抗生素(10 μg mL?1 甲氧苄啶,3 μg mL?1 四环素),并在开始成像和改变流速之前让其在通道中流动 10 分钟。强流以阶跃函数的形式施加:从 0 μL min?1 开始,然后变为目标强流速,然后再次设置为 0 μL min?1。由于压力控制器对流速加速的限制,从 0 增加到 2000 μL min?1 并使微流体通道中的流速稳定下来需要 15 秒,这是该系统中可达到的最大幅度。同样,将流速从 2000 μL min?1 降低并稳定回 0 μL min?1 也需要 15 秒。在 3 个时间点对 3D 生物膜体积进行成像:施加强流之前、强流期间(流速增加 1 分钟后)和流速降低 1 分钟后(图 1A)。作为实验参数,生物膜暴露于不同的最大流速(100、200、500、1000、2000 μL min?1),或者使用不同体积 V 的生物膜(519 μm3 < V < 6032 μm3),或者改变高流速的持续时间(3、5、10、20、40 分钟)。每个生物膜变形测量都是在不同的微流体通道中对之前未暴露的生物膜进行的。
参考文献:
T. Ohmura, D. J. Skinner, K. Neuhaus, G. P. T. Choi, J. Dunkel, K. Drescher, In Vivo Microrheology Reveals Local Elastic and Plastic Responses Inside 3D Bacterial Biofilms. Adv. Mater. 2024, 2314059. https://doi.org/10.1002/adma.202314059
扫描关注微信公众号,随时了解更新信息!
扫描关注,随时沟通。
全部评论(0条)
推荐阅读
-
- 体内微流变学揭示了三维细菌生物膜内部的局部弹性和塑性响应
- 细菌生物膜是大量存在的三维活性物质,具备执行复杂的生物力学和生物化学功能的能力。此文在不同的应力振幅、周期和生物膜大小等条件下,对霍乱弧菌的活体三维生物膜内的数千个细胞进行了追踪,揭示了细胞位移和细胞重新定向的各向异性弹性和塑性响应。
-
- 微电极检测不同光强下生物膜内部不同深度的DO浓度,揭示微藻生物膜生长的调控机制
- 微电极检测不同光强下生物膜内部不同深度的DO浓度,揭示微藻生物膜生长的调控机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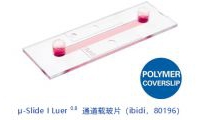
- 手把手教您制备可视化的细菌生物膜和扫描电镜SEM标本
- 本应用阐述了使用 µ-Slide I Luer 0.8 通道载玻片(ibidi,货号80196)在静态条件下培养细菌生物膜,并通过共聚焦激光扫描显微镜(CLSM)与扫描电子显微镜镜(SEM)联合成像的
-
- 电子洁净室局部微环境系统
- 电子洁净室局部微环境系统
-
- 锂离子电池的机械测试,究竟揭示了什么?(下篇)
- 本文深入探讨了锂离子电池在机械测试领域的三个关键环节:剥离、粘合与摩擦测试。
-
- 锂离子电池的机械测试,究竟揭示了哪些秘密?(上篇)
-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深入探讨了锂离子电池在机械测试方面的各种方法,这些方法对于电池性能的评估和优化起着决定性作用。
-
- DWS微流变学用于化妆品配方设计—Rheolab应用
- 摘要由于光学微流变技术可以将频率范围扩展到高频并深入了解蠕虫状胶束和其他复杂流体系统[1,2-8]流变学和动
-
- 附生生物膜活性对海草叶光合活性、pH 和无机碳微环境的影响
- 附生生物膜活性对海草叶光合活性、pH 和无机碳微环境的影响
-
- 会议提醒 | 用电子显微镜和X射线微CT揭示电池创新
- 今晚10点,未注册无回看,先点上!前沿技术不错过。
-
- 揭示高精度三维形貌测量在有机光电器件中的应用
- 揭示高精度三维形貌测量在有机光电器件中的应用
①本文由仪器网入驻的作者或注册的会员撰写并发布,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仪器网立场。若内容侵犯到您的合法权益,请及时告诉,我们立即通知作者,并马上删除。
②凡本网注明"来源:仪器网"的所有作品,版权均属于仪器网,转载时须经本网同意,并请注明仪器网(www.yiqi.com)。
③本网转载并注明来源的作品,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不承担此类作品侵权行为的直接责任及连带责任。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转载时,必须保留本网注明的作品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
④若本站内容侵犯到您的合法权益,请及时告诉,我们马上修改或删除。邮箱:hezou_yiqi
























参与评论
登录后参与评论